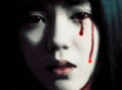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一)
我第一次和艾琳说话是在中学时期的一次舞会上。她太受欢迎了,所有人都想跟她跳舞。我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插队进去。你们可要知道我那时是什么样的:非常害羞,总担心自己表现得太胆小。就这样迟疑踌躇了半天,我终于得偿所愿,但我们只跳了几分钟,很快又有别人插队进来了。
有一次,艾琳邀请我去她家。当我到她家的时候,艾琳正在为她的哲学课作业发愁。她说:“我们的老师总是提醒我们,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有正反两面。”
“你们老师的这句话本身也有两面。”我说。
“什么意思?”
我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莫比乌斯环”。那时,莫比乌斯环并非人人皆知,但是很好理解。我拿出一张纸条,扭了半圈后将两头接上,做成了一个环。艾琳看到后很兴奋。
第二天的课堂上,艾琳就等着老师说那句话。果然,老师拿起一张纸说:“任何问题都像纸一样,有正反两面。”这时艾琳拿出手中用纸条扭成的莫比乌斯环说:“老师,您的这句话也有正反两面——我这里就有一张只有一面的纸!”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很惊讶,艾琳颇有成就感地展示了莫比乌斯环。我觉得,自那以后,她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不久,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又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每逢假期我都回家见艾琳。有一次,我去看她,她的颈部鼓起一个肿块,肿块不断变大变小,医生说问题似乎出在淋巴系统。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医院的一个医生告诉我们,艾琳极有可能患了何杰金氏病。他说:“病情可能会出现反复,逐渐变糟。现在还没有办法根治,艾琳大概还能再活两三年。”
面对如此大的磨难,艾琳却表现得很冷静,竟然很快考虑起了下一个问题。“好吧,”她说,“我得了何杰金氏病,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虽然博士还未毕业,但我已经在贝尔实验室谋得一份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在纽约皇后区租一套小公寓,离医院和贝尔实验室都不远。我们可以在纽约结婚。那天下午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有了新计划后,艾琳去医院对脖子上的肿块做了活体组织检查,以充分确认病情。几天后,艾琳打来电话:“化验报告出来了。诊断结果是,淋巴结核。”艾琳还说:“这样我也许能活7年,可能还会好转。”自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能一起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件事后,一切问题都难不倒我们。
(二)
“二战”爆发后,我受聘加入了“曼哈顿计划”,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几个月之后,一拿到学位我就跟家人宣布,我要结婚。
我们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堡找到一家慈善医院,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艾琳可以在那儿就诊。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我借了一辆车,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改造成救护车那样,这样艾琳累了的时候就可以躺一会儿。我开车去艾琳家接上我的新娘。跟艾琳的家人挥手告别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穿过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乘轮渡前往斯坦顿岛——那就是我们的浪漫邮轮之旅了,然后到市政厅登记结婚。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会离开普林斯顿去看艾琳。
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盒铅笔——墨绿色的笔杆上有一行金色的小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小笨瓜。”是艾琳寄来的(我叫她“小笨瓜”)。这很甜蜜,我也很爱她,但是铅笔总是会被人随手乱丢:比如跟魏格纳教授讨论某个定律或问题后,我就很有可能把铅笔落在他的桌子上。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
那时我们并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我从浴室找了个刀片,刮掉铅笔上的字再用。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开头写着:“为什么要把铅笔上的字刮掉?”接着是:“我爱你,你不觉得自豪吗?”后面继续写道:“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所以我还能怎么办?只好直接用印着字的铅笔。
不久,我被调往洛斯阿拉莫斯。项目总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给艾琳安排了离那儿最近的一家医院。我每个周末休息时就去看她。工作日时,我经常收到艾琳的来信。有些信会做成拼字游戏的样子,剪开后装进袋子寄过来。我收到的时候信上附着检查信件的军官写的便条,内容多半是:“请转告您的太太,我们没时间玩猜谜游戏。”
艾琳虽然身处小房间,心却在全世界。我为艾琳能乐在其中而感到开心,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三)
时光流逝,艾琳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她的父亲从老家来看她。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找我,说:“你最好马上过来。”
等我见到艾琳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意识也有些模糊。她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多数时候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偶尔看一下旁边,呼吸困难。
我出去走了走,惊讶于自己仍旧很平静,这不像想象中最后时刻该有的情绪。可能我在欺骗自己。我心情低落,但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也许是因为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
这一点很难解释。如果火星人(假设他们除非意外不会自然死亡)来到地球,看见人类这种特殊的生物——活了七八十年后,死亡必定降临——火星人肯定会觉得,在明知生命短暂的情况下活着,真是一个可怕的心理重负。是的,我们人类知道如何面对这个难题:我们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琳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50年,而我们只拥有5年。这只是量的区别,面对的心理重负却是相同的。除非我们觉得“那些拥有50年的人更幸福”,那么才确实有区别。可是那种想法太奇怪了。为什么要抱怨“我怎么这么倒霉”,来让自己变得更痛苦呢?如果你明白了现实,并发自内心地接受它,便绝对不会有上述种种抱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所经历的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偶然。我和艾琳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
我回到她的房间。我不断想象着那些正在发生的生理变化:肺不能将足够的氧气带入血液,大脑因为缺氧导致意识模糊,心脏也因为缺氧变得无力,这又让呼吸更加困难。我一直猜测会有一个全面崩溃的时刻——所有器官骤然停顿。但这一刻没有出现,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越来越弱,直到再也没有任何气息。
值班护士走进来,确认艾琳已经去世,然后就出去了。我静静坐了一会儿,走上前最后一次吻了她。
我很诧异她的头发还是原来的气味。当然,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头发的气味不应该有变化。但这在当时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段时间,我一定对自己采取了什么心理干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直到大约一个月后,我经过橡树岭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琳会喜欢它的,顿时,泪流满面。
作者:理查德·费曼 印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