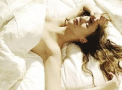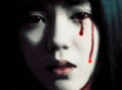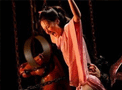松明照亮的夜晚
有时是碾米坊。
有时是木材厂。
有时是宽敞的晒谷场。
晒谷场上的机会很少。一般只有老人大寿,孝顺儿女包一场电影,放给全村人看,这才会摆出来,在晒谷场上公然放映。鞭炮声召唤远近的人们前来。放的电影喜气洋洋,其中必有一场是越剧《五女拜寿》。另外一场好看得多,很可能会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喜欢的武打片。幕布的两边都会坐满人。在山村幽蓝的夜空下,当剧中人举起手枪射击,靠山边的人看见他是右手举枪,而靠河岸的人则看见主人公是一个左撇子。
碾米坊也不是常态。只有当木材厂堆满了木头,放电影活动实在无法开展之时,碾米坊才会被考虑启用。碾米坊内四壁皆是尘灰,有人走动时,震动起的尘埃是米糠碎末的气息。但是碾米坊至少有门,可以方便把控,只有买了票的人才被允许进入。碾米坊实在狭小,很大一块地方让给了老旧的碾米机。碾米机靠河岸下的水流冲刷,来带动机械部件吱吱呀呀地旋转。在电影人物悠闲地走动,或是艰辛地思考之时,碾米机就会不失时机地吱吱呀呀起来,为剧情配上合适的音乐。
最好的场地是木材厂。www.dyulu.com
木材厂宽敞,也有门。窗子高而窄小,试图逃票的人完全爬不进去。在没有伐木计划的时候,这是最适合放电影的地方。
一排排的长条椅子就靠在墙边。有的条椅腿断了,随便找一块木头钉起来,跟原来的一样结实。人们一排排地坐在这样的条椅上,整整齐齐。电影一开始,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人们专心于别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记得那部叫《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台湾彩色故事片,让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在一排排的长条椅上流眼泪,甚至有人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在闪烁的光柱里,我看见放电影的人也哭了,力大如牛能扛两百斤木头的二舅公也抽抽噎噎。我也哭了,但我努力遮掩,生怕被别人看见或听见。
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那场电影在村里一连放了一个星期。
有人连续流了七天眼泪,因而心满意足。
我已经忘了放电影的人是谁,面孔如何。我甚至忘了看过哪些电影,也忘了电影的票价是多少。那时候我只有十多岁,还在上小学。我的暑假都在山里的外婆家度过。我只记得一个又一个山村的夜晚,我被小舅、表哥、表姐领着,沿河走三四里的土路,去另一个村庄看电影。
那时外婆家条件并不好,舅舅和表哥们也难得有什么零花钱,哪有钱经常看电影呢。我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时候,山里的人们,经济状况都差不多。每场都有那么多的观众,想来电影票的价钱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晚饭后,人们隔着河岸相互呼喊对方的名字。“吃饱了吗?吃饱了就走哇,电影要开场喽。”“你再等等。”“不等了,我前头走,你后脚来。”
河里的水,是高山上淌下来的溪涧水,一路呢呢喃喃。河岸上的人在走,要去三四里地外的木材厂看电影。今夜放的是什么电影,他们早已知晓。头天电影散场的时候,木材厂墙外边就会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彩色宽银幕武打故事片。
这激动人心的字句,要在人们的心头记挂一整夜,又一整天。现在,还要记挂一路。这样的字句,就像现在的人们看到的3D效果一样,不,比3D效果更富有想象力和冲击力,一路撩动小舅舅和表哥们的心弦。
我跟在小舅舅和表哥们的后面,走着山路去看电影。
山村的夜晚,有月亮的时候很亮,没月亮的时候就很黑。
我有四五个舅舅,最小的舅舅当时才十六七岁,白天经常上山砍柴。
他会把松明留下来,晒干。去看电影的路上,他在裤兜里揣一块松明。
什么是松明?山松多油脂,劈成细条,燃以照明,叫松明。
晒干的松明最宜于在很黑的夜晚使用,照亮我们去看电影的路。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天色尚早,朦朦胧胧。对山里人来说,完全用不着任何照明设备,他们的眼睛如夜鹰,熟悉大山的每一处犄角旮旯。松明只在回家时用。
回来时路更黑。小舅会燃起那块松明,举着它,把我们一路带回家中。在石蛙的鸣叫里,在一连串的犬吠声中,那块燃着的松明,会让我们仍然沉浸在摇曳的故事当中,一路都无法自拔。
小山村的每一个夜晚,都那样令人期待。
在日常艰辛的劳作之外,在上山砍柴、下地劳作、入林伐木及各种各样的挥汗如雨、筋疲力尽之后,小舅舅和表哥们,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仍然充满力量地行走在山村的小道上。
去晒谷场、去碾米坊,更多的时候,是去木材厂。
我十岁还是十一岁的一个夏夜,在去木材厂的路上,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从朦胧的河岸上摔了下去,至今我的右额仍留有一个半指长的疤痕。
它与电影有关,与文艺有关。因此它虽然很难看,但我并不讳言,也从不曾想刻意遮掩。
那个夜晚,小舅舅和表哥们把我从乱石河岸边捞上来,找了一块手帕简单包扎,然后我们便继续前行,去往木材厂。我顽强地看完了那场电影。
我的额头至少包扎了一个月之久。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但肯定磕伤了颅骨。整个过程没有经过任何检查,只是将各种草药混合研碎包裹在手帕里,捆扎在伤口上。一个月之后,我的伤口成功愈合。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了一部短片,那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放映。时隔多年之后,它让千里之外的一个山村少年从河岸上摔了下去,右额因此留下一个永不消退的疤痕。
那一夜,电影依然摇曳,松明依然摇曳。
作者:周华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