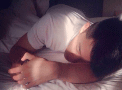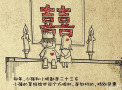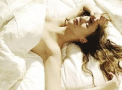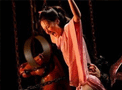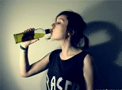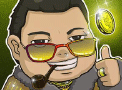虎子无犬父
1900年注定不安分,中国北方正闹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有位老公子哥不得志、很郁闷,冷冷清清地来到南京,打算在这里定居养老。南京这地方从来不适合韬晦养志,任你是个什么人物,灯红酒绿的秦淮河边一住,革命也就基本到头。
这位老公子哥便是散原老人陈三立,说他老,他此时48岁,按照古人标准,确实没多少年折腾了。说公子哥,他是晚清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两年前戊戌变法,出身名门的四位公子,呼风唤雨何等风光,不曾想风云突变,维新人士成了康梁乱党,“维新四公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押往菜市口砍头,其他三位没掉脑袋已算幸运。
“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既然政治不好玩,会丢了身家性命,散原老人开始全心全意地玩文学,玩纯文学。当时的文坛,说白了就是诗坛,小说是标准的俗文学,给下里巴人的老百姓看,士大夫和文人看重的还是有传统的诗歌。谁在诗坛上最牛,谁就能执文坛之牛耳。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散原老人尊为“及时雨宋江”,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一,由此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要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真犯过什么严重错误的话,就是没把这奖项颁给俄国的托尔斯泰,并且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个散原老人。毫无疑问,作为诗坛祭酒,作为当时中国文坛最有代表地位的诗人,如果他老人家获奖,不但众望所归,关键还能增加这个文学奖的含金量,毕竟中国传统诗歌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中谈到诗坛,虽调侃,也写出了当时的部分真相。一位叫董斜川的诗人吹嘘自己曾跟散原老人聊过天,说“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认为“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小说家的话不可以太相信,当不得真,不过玩旧诗,通常倚老卖老,会看不上新诗,新诗人却不得不对前辈表示恭敬。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慕名拜访散原老人,散原老人比泰戈尔大9岁,也算是同时代人。徐志摩屁颠颠地给他们当翻译,免不了一些客套,相互送书,拍照,究竟说了些什么话,有过什么样的文化交流,也不得而知,反正多少有点象征意义,毕竟当时中国和印度最好的两位诗坛大佬见面了,这很不容易。
有人问,既然对散原老人有兴趣,那么他当时住的老房子在哪儿?我想了想,真答不出来。九曲青溪十里秦淮,只知道紧挨青溪河边,取名“散原精舍”。“精舍”二字望文生义,容易让人联想豪宅的精装修,其实是普通住宅。古人称佛教修行者的住处为精舍,散原老人官场失意,避祸南京只为养老,用这两个字十分合适。
那时候,陈寅恪只有10岁,有兄弟5人,最小的登恪刚3岁。散原老人为了儿子的教育,干脆办家学,花银子聘请家庭教师。他身上洋溢着名士气,俨然成了《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饮酒作诗,基本上就是专业作家。科举还没废除,他早已大彻大悟,内心深处先将它给结束了。
有人把清王朝的崩溃,归罪于科举废除,因为读书人失去了奋斗目标,前途变得黯淡了。散原老人也算是有功名的人,举人出身,中过进士。1882年乡试,30岁的他讨厌八股文,竟用散文体写试卷。这是公然冒犯科举,初选就险遭淘汰,幸好遇到一位慧眼识才的考官,重新将他破格录取。
僵硬的科举已失去存在意义,废除不废除都得完蛋。只是他的做法,更像一位纯粹的诗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气质,才能把诗写好,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现成的例子就是陈寅恪,他显然继承其父风范,学贯中西,不知念了多少个第一流大学,学历上可以写上日本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能阅读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却没有任何正经八百的文凭和学位。
在科举废除的前两年,也就是1903年,散原老人曾担任过南京三江师范的总教习,又称总稽查。三江师范后来改名两江师范,又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再改名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最后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因此,说起南大的老校长,似乎不该忘了提一提这位散原老人。不过这也是挂名差事,他显然志不在此,这时候,北京已经有了京师大学堂,各地纷纷效仿,由官方出面办新式学校,官办学校就像官样文章,通常不入诗人的法眼。
散原老人更像是一个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物,好在有个争气又充满传奇的儿子,你可能不认识散原老人,但你不会不知道他的儿子陈寅恪。
作者:叶兆言 来源:中信出版社《陈年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