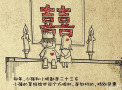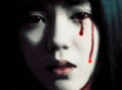命运帮她收了场
还想再跑跑,可是命运不答应了
人其实保留着一些兽性
深爱一个人短暂的机缘,和深深了解一个人漫长的情谊,若是你,会愿意得哪一样。
有时江柔想起陈桉还是会觉得自己足够运气,虽然如宋晓这样的旧友都无法理解怎么十多年了,细胞都代谢过一轮了,还绕不过一个少年恋人。
只是她们提起陈桉啊,时间像回来了几年,那个陈桉啊,漂亮极了的陈桉,虎头虎脑在讲台上背李白的诗。从前她们爱说:陈桉,我给你写的情书呢?陈桉,让我看看你的酒窝。这么想起来,陈桉像她们一个共同的美梦,混着樟脑般回忆的苦香。
宋晓吸一口十多年后的空气,像梦醒,对着江柔说:“不怪你那么喜欢他。”
她们高三的那次毕业旅行,浩浩荡荡一行九人前往西塘。年轻人看着也让人觉得生机勃勃,好像试卷还装在书包里,未来已经在脚下了。江柔是班长,一路像个家长管理着班费,管吃管住,煞有介事。他们夜宿客栈,一幢独门独幢的小别墅,5间房间干净敞亮,一楼有个院落,一株石榴树开得太好,掩映着小厨房。陈桉他们四个男生简直乐疯了,买来啤酒零食,迅速占据有利位置,赌虫上身,大战八十回合。女生结伴出去买菜,又挤进厨房,锅碗瓢盆一通响。夕阳落下来,金粉般的夕照撒在一只瓷碗上,好像盛了一碗金水。陈桉的手刚好伸过来,捞起碗冲着江柔喊:“班长,我好饿啊。”江柔一晃神,这一声好饿,后来她差不多听了有十年。
他们在西塘住了三天,最后一晚在酒吧给陈桉送行,闹得太疯,集体喝趴。勾肩搭背地一路唱着歌,踩着青石板上的月光回来。陈桉在江柔的左手边,同样瘦弱的肩膀揽着她的脖子,近得闻得到他身上小兽般的汗味。书上说人其实保留着一些兽性,若喜欢一个人,总爱闻他身上的气味。
五间房九个人,江柔享有小特权,一个人睡在一楼最靠院子的那间。
临出发的那个清早,下起细雨,隐约听到有脚步声。蟹壳青的天色里,陈桉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乌黑的头发,瘦弱的样子,一些年以后江柔回想起来,少年低头护住烟的样子,那么温柔。所谓落花微雨人独立,也大概就是写的这样吧。
他推门走进来,光着上身,撒娇般喊冷,钻进她的被窝。瘦瘦弱弱的,像个佛前青灯的小和尚。他抱着她静静说了会话。陈桉高中毕业后去英国,江柔则考上上海的大学。少年时的告别没有那么多愁绪,他只是把下巴抵在她的头顶,加深了这个没有沾染一丝情欲的拥抱。
被温柔包裹进松泪的昆虫
英格兰以北,天地都太宽广,草地、牛羊、格子花纹、风笛音乐,还有到处能买得到的威士忌。月色太凉,陈升的歌又满是乡愁。陈桉觉得孤单,给江柔写长长的电邮,词不达意,在结尾处才言简意赅地附上一句:“你敢不敢谈异国恋。”
两天后收到江柔的回信,是整整一个G的菜谱压缩包,分早中晚三餐,全都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周没有重样。苏格兰是日暮,总有辉煌的落日,陈桉心有震动,被那封电邮定在夕阳里很久很久,像被一只被温柔包裹进松泪的昆虫。
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年多,陈桉记得江柔对他很好,好得细碎又温暖。
他记得他有次回国参加一家外企的寒假实习生面试,前一晚江柔陪他住在校外的小旅馆里准备面试资料,各种不顺,偏偏还打翻了泡面弄脏了面试的西装裤。他冲江柔发了一通脾气,借口买烟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看到她已经把裤子洗干净,不知从哪里借来一台老式取暖机,安安静静坐在床头耐心地把裤子一点点烘干。暖黄的光笼着她,水分慢慢变成袅袅白雾往上蒸腾,小旅馆里简陋的背景也染上了一种很温柔的情愫。
陈桉的心在那一刻好软,他不发一言,走过去很眷恋地把她抱进怀里。
好像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拥抱多余亲吻,依恋多余爱,这在年轻时是多么不合时宜。陈桉在留学生圈子里认识越来越多青春昂扬的同类,他们驾车去美国西部的黄金海岸,敞篷跑车、妙龄女郎,酒精、沙滩、音乐、迷幻剂,当他的生活出现越来越多的层次,江柔被抛弃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江柔是在清晨收到陈桉的分手邮件,语气措辞是全世界通用的那种分手格式。她握着手机呆呆地坐在宿舍的上铺,宋晓喊了她几遍都没有回应,爬上去一看,满脸的泪水,哭得像个被喊醒的做着梦的孩子。
可能是心有眷恋,也可能是余情,他们没有成怨侣,而是渐渐就退回到当年好朋友的位置。似君子之交,不亲近又不至淡漠。
每年会在同学聚会不多不少见上两面,那几年,陈桉越来越少年意气,江柔则像一只蚌,慢悠悠地合起来,藏掉所有的锋芒。可是他们俩并肩坐着,一个伸手布菜添饭,一个在喝醉后轻轻抚上一块热毛巾,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令宋晓这样的知情人不胜唏嘘。
然而江柔的心,那么明明白白,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爱情让人委屈得忍不住想哭。
命运给了你那么多暗示
2008年陈桉回国,渐渐和一些旧时好友恢复来往,一起约着去北京看奥运。曾经的英雄刘翔在那一年退赛,现场好多人都哭了。
江柔哭得特别厉害,连她自己都没明白,怎么会那么难过。
陈桉回国前,江柔有去苏格兰找过他一次,那时他刚结束上一段感情,身边终于空旷,裹一件长羽绒服,带绒线帽子,只留出一对眼睛,好像很怕冷的样子,恹恹地来机场接她。
他借宿在苏格兰当地居民家里,幽深的屋子,丰盛的酒窖,他换上天蓝色的毛衣钻进厨房,手脚利落地为她做出一盘西餐。
又开了两瓶84年的赤霞珠,苏格兰盛产威士忌,舶来的葡萄酒也是美味又价廉,简直是爱酒之人的天堂。他们点着了壁炉,一同裹着条厚毯子,席地而坐,喝酒。什么都不用说,情义都在酒里。
放不下又回不去,让人徒然伤感。后半夜突然停电,陈桉默了默,说:“我们来打个赌吧,如果天亮了电还没有来,我们就重新开始,怎么样?”
黑夜似一块磁石,一点点吸收着周围的光,窗外鹅毛大雪,室内越来越冷,他们等得快要睡着,噔一声,墙上、头顶的灯一齐亮起,明亮似白昼。江柔站起来,冲陈桉难看地笑了一下,转身往客房走。那一瞬,她才回味过来,2008年为什么那么哭,她爱陈桉的心境和刘翔退赛时哭是一样的,还想再跑跑,可是命运不答应了。命运给了你那么多暗示,好言相劝让你停了,该收手了。
第二天她回国,陈桉送她去机场,抱了一抱,各自松手,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往来。
2009年江柔回到了无锡,在北仓门开了一家叫东久的汉式按摩馆,古色古香。有一个叫高山的祖传推拿师傅,相貌实在出众,人高马大,走路虎虎生风。穿素色的唐装,袖子挽到手肘处,手艺如行云流水。馆内有艾草沉稳的气味,水沉香袅袅的白雾,师傅的手拍打在肉体上浸着汗的声音,被门口一大幅半年成的双面苏绣挡住,隔间的小厨房,隔水蒸着玉米、山药等粗粮……江柔总是想起这样的情景。
她坐在长条案桌前拿计算器噼里啪啦算账,酸痛的肩膀搭上一双手,轻柔又力道恰好地按着。不用回头,便知道是高山,搭上一只手,又把脸颊温顺地贴上他的手背。她和高山在一起将近一年,高山的好在于他的不深究,知晓喜欢是乍见之欢,爱是久处不厌。他对江柔和陈桉之间的小情小意视若不见,对自己的过去同是讳莫如深。
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隐去了绝世武功,安于当藏经阁的扫地僧。
对一个人好是会上瘾的
陈桉回国后也留在无锡,有时会来东久看看江柔。他酷爱抽烟,江柔就总去隔壁的咖啡店讨一些当日的咖啡渣,装在一个椰壳做的烟灰缸里给他装烟蒂。他们之间没有亲密动作,很多时候就是这么面对面坐一会,他抽几支烟,她在对面静静陪着。陈桉最初创业,心事太多,总是锁着眉。
拿起车钥匙说要走,她也不留,伸手抚抚他的眉头,说得空再来。
他走了,茶凉透,她还坐在外面舍不得进来。高山看在眼里,什么都不说,拿一件外套搭在她的肩头,回屋继续招待客人。
对一个人好是会上瘾的,这个道理,江柔懂,高山更懂。
岁月幽微曲折,爱一个人淡淡的情义。出自同一棵古树的两串小叶紫檀,两人分戴着,像走了心一样。陈桉应酬在厕所在浓妆艳抹的女郎手掌下吐得像条狗时,江柔有时也会跟着莫名其妙地不舒服,将原本就空的胃吐得空无一物。有时午夜梦回,一脸庞的眼泪,给陈桉发信息:我梦到你出事。他若方便,会立马回个电话过来,阳奉阴违地说着没事没事,继续回酒桌与人称兄道弟,笑得暧昧不明。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会永远少年白衣,中年是种风尘,总会沾染。
有次他们集体出游,夜宿在青岛,夏夜、冰啤酒和大只大只的海鲜。陈桉有些喝醉,去墙脚吐完走回来还要摇头晃脑地向大家鞠躬谢幕。江柔沉醉在那种氛围里,看了他一眼,把头扭到别处。有抱着吉他30块唱一首歌的妙龄少女,甜美的声音唱沧桑的歌:“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来来回回一句可不可以,像一个怎么都不肯死心的人,陈桉手抖着烟差点拿不住,宋晓扶扶他的肩,高山醉倒在桌上,从前的陈桉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样的成年人,只有在喝多的时候,眼眶会湿,心肠会软。他举起右手,和江柔轻轻碰了碰杯。江柔笑了。
在27岁就对前程不抱期待,想着就这样过完一辈子吧,有情有义地待彼此,起落都在一旁相伴,适宜地伸出一双手扶一把。江柔在杂志上看到冯唐的诗:草木都美,人不是;中药很苦,你也是。心底也涌起一种莫名的凄凉,别人不需要去懂那些苦涩的前因和回不了头的艰难,他们只要结果。江柔不是,她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她不哭,愿赌服输。
这个大骗子再也没有回来
陈桉28岁志得意满,乔迁新居。请大家去家里做客,新谈的女友浓情蜜意,似要谈婚论嫁。一大帮人闹到最后,醉了大半。江柔去厨房煮蜂蜜水醒酒,恍恍惚惚地坐在灶台前等水沸。陈桉走进来,隔着长长的餐桌和她面对面坐着,对视了一会,都笑了。
他说:“这个厨房是照我们以前说的布置的,以后可以几家人一起来烧烤。”
她说:“有一天你结婚,千万不要喊我。
2014年3月6日,陈桉结婚。江柔在那之前决定出去旅行一段时间,散散心,也决心彻彻底底放下一些东西。婚礼那天因为飞机延误江柔没有到场,宋晓在花海般的宴会厅待了半个小时也忍不住走出去吹风,眼眶微酸,像一段岁月的终结,路归路,桥归桥,她在心里感慨,幸好江柔没来,来了得多难受啊。想起从前江柔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当然要去陈桉的婚礼啊,还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让他的那一位知道,我们陈桉是很受欢迎的,得上心,必须疼他重视他。”
然而江柔这个大骗子再也没有回来,3月8日以后铺天盖地的马航失联客机的报道,227位失联乘客中,她的名字赫然在列。
个人的悲剧是无法抵御一个属于时代、国家的更大的悲剧的,高山、宋晓赶去北京,在丽都酒店前前后后死等一个星期,侥幸、期待,心灰意冷又希望重生,最后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死了。一个人就这样没了,新闻发布厅里突然有死者家属情绪失控,号啕大哭。蜜月赶回来的陈桉那个时候冲进来,明亮的日光灯打在他脸上,一脸的死白。
和美长久里本来也没有她
很多时候,死亡是很残酷的。年迈的老黄狗睁着浑浊的眼睛看老主人提着屠刀走向它,顺从地低下了头,变成了灶台上香喷喷的一锅狗肉,硬得像木柴。猫死了,没人要它,就装在黑塑料袋里挂在河边的树枝上。
麻雀叼走它的眼睛,然后是酸酸的肉,最后只剩下一张软塌塌的皮。
人的死亡,并不比这些来得温和。哪怕她死于青春,也同样凄惶。
像江柔缺席他的婚礼一样,她的葬礼也没有陈桉的身影。黄昏的时候,高山在东久的院子里找到他,灰色的毛衣,坐在一株石榴树下,背影一动也不动。高山从前说过,一个院子里只有一棵树不好,就是一个困字。可江柔,独爱这一株石榴。
夕阳越来越暗,陈桉蜷缩在那张藤条椅子里一动不动,听到高山喊他,茫茫然地回国头,那神情,好像一个失落了很多快乐的少年。
“她可能有预感觉得自己回不来,走之前就给你准备了礼物,还有一张贺卡。”陈桉拆掉精致的包装,是她最后的字迹:愿往后的日子,和和美美,长长久久。
和美长久里本来也没有她,她诚意地留下祝福,命运帮她永远退了场。
文|陆小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