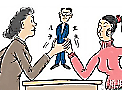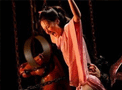还可以游啊
鹰问鱼,可你是怎样来到这儿的呢?
鱼说,我的翅膀被射中,跌落谷底后又变回了鱼,
幸运的是,那是一条通向大海的河,
我想,我原本就是一条鱼啊,我还可以游啊,
你瞧,如今我们又是一样的了。
2009年初,父亲病逝,我大二,休学一年回到沈阳老家,陪伴母亲走出阴霾。因家境大变,一年后再次回到香港,惊觉自己已负担不起当时较为昂贵的学杂费用,写作赚到的那一点钱仅够维持基本开销。为免母亲忧心,我选择自食其力,但非常反励志的现实是,我根本无力自食:想打工,香港政府不允许留学生打工,抓到就遣返;想创业,没商业头脑,试做过小生意,把手头最后那点钱也赔光。
生活中多少未经思考的美好,都是习以为常的毒药。我一直相信,人只有承认对生活本身的无力以后,才是真正获得勇气的开始。我的勇气用在了借高利贷上,而且是在香港。都是从小看《古惑仔》长大的一代,八年前初赴香港前,表哥表姐还特意叮嘱我,到那边千万别惹黑社会呀,见到大街上砍人躲着点走呀,血迸一身用淘米水洗呀。但只要在香港生活过就会知道,那是一座被影视剧严重歪曲的城市,单就社会治安,安全系数亚洲前三。我当然想不到,几年后的自己也会跟“高利贷、黑社会、古惑仔”等港片名词发生真切的人生交集。
借高利贷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你不会一上来就跟左青龙右白虎、张口闭口“屌你全家”的浩南山鸡们打交道,而是一些利息高过大银行的小型信贷公司,他们有途径查到你信用卡里欠多少钱,获取你的电话号码,然后主动打电话要借给你钱,和和气气,这些人不过是在小公司里讨生活的普通职员,当你借了他们的钱却不能按时还上时,起初几个月还是这些人打电话来催账,仍和和气气,但无论你以什么借口仍还不上,再来找你的,就是他们雇用的催债公司了,俗称黑社会。“追债仔”会先给你打几通“问候”电话,说些“知道你家住哪里”“放聪明点”之类的话,只要心理素质够好,是可以当耳旁风的。但接下来,追债仔就会找上门,先在你家邮筒里投放恐吓小纸条,一段时间后若你仍无动静,就要在你家大门上泼油漆或者刷上“还钱”两个大字,跟港片里演的一样。
当时的住处是我跟室友合租的,那段时间我刚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最初借的十二万块钱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利滚利已接近二十万,欠了几个月的利息没按时还,恐吓电话和小纸条都已收过,估计该来刷油漆了,我怕室友受惊,他每天出门上班,我则守在家里哪也不去,早中晚各开一次门检查,终于被我及时发现门上的“还钱”二字,字不大,估计追债仔也是刚下海,资历尚浅,社团配给的油漆有限。于是我赶在室友下班回家前用信钠水擦干净了,室友至今不知情。
一开始当然是怕得要命,每天出门下楼都要前瞻后顾,脑海里挥之不去《古惑仔》电影里黑色厢型车急停于面前,三五个黑衣人冲出来把自己绑了的画面。幸好,街对面十米处就有一家7-11,我用身上最后的零花钱的一半买了足够半月不用出门犹可度日的泡面,捧着回到住处,紧锁房门,再拉上铁闸门,听音乐看电影一律用耳机,假装房内无人。又过了好多天,反而风平浪静,自己也渐渐不那么紧张,转而又安慰自己,也许追债仔也休年假呢,更何况自己在香港无亲无故,名下又无房产和存款,连工作单位都还没有,光脚不怕穿鞋的,又不能真拿我怎么样,堂堂社团,怎么也不至于为区区二十万要我的命吧。
再后来,我居然在一家常去的小饭馆吃饭时跟一个古惑仔常客混成了熟人,他是老板的朋友,而他的工作恰恰是追债仔。熟人透露“行业内幕”说,五十万以下的账基本都是坏账,大家心知肚明,人消失了公司都懒得追,本来就没什么赚头。从此我更加坦然,甚至有一次追债仔疯狂地在外面砸门,我还在里屋塞着耳机写东西。
在那之后不久,我找到一份还算凑合的工作,工资起码可以填补每个月要还的最低利息,追债仔也暂时放假了。但我因不喜欢坐办公室,每天都过得万分压抑,渐渐染上酗酒的毛病。每晚下班回到家必须喝到烂醉才能睡着,第二天再浑浑噩噩地爬起来去上班,终于在三个月后患上盲肠炎,被送到医院开了一刀,住了三天院。出院后,我清楚自己不可以辞掉工作,那点工资起码能买一份清静,只要不被追债仔烦,每天就还能有点时间做喜欢的事,例如写作。病痛给了我警醒,恢复后开始减少饮酒,尽量控制,靠写东西来缓解酒瘾。
那段时间,我总是想起已经离世三年多的父亲,而他在世时,我们几乎从不交流。他本就没什么爱好,只爱喝酒,心底该是有多少我不曾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的愁苦。我曾在他去世后决心写一个关于他与父辈们的故事,但苦于被生活中的其他事困扰,深陷长达两年的瓶颈期,写那个故事的念头被一再搁浅,乃至放弃。想不到两年后,在自己人生中最窘迫的一刻,竟无法抑制地想起他,惦念起那个故事,重新开始写作。我用一年的时间把故事完成。那一年里,我漫无目的地工作,拆东墙补西墙地还利息,若无其事地跟朋友们团聚,用借来的钱请客吃饭。至于背后实情,始终无人知。直到债务全部还清后,我才跟母亲提起那几年的经历,母亲心有余悸地问,那你有没有担心过,要是到最后都还不上那笔债,该怎么办?我说,那就跑路吧,跟港片里演的一样。
2013年底,新书出版半年后,故事的影视改编权被某家影视公司买去。版权费还算可观,一次性还清了债,并成功帮我从坐办公室的日子中解脱出来,不必再为还利息而出卖自由。剩下的钱,给我在香港最要好的朋友都买了礼物,又带着母亲出去游玩了两趟,那笔钱最后也就没剩多少。之后我便离开香港开始各地辗转。有朋友得知这一切后问我,那一切结束的时刻是不是有刑满释放的解脱感?我说不是,那感觉是两清,跟这座城,跟那几年,两清。
此后每每跟好友谈起那两年的经历,我都不愿矫情地说,那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因为无论怎么回望,那些不堪都不可能如财富一般美好。但那段经历的确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生必经的形态有千万种,一飞冲天也好,连滚带爬也罢,自愿抑或是被迫,生命若不息,只要还在路上,人总是在向前行的。
讲到这里,似乎自己最窘迫的那几年里发生的一切,都没任何必然联系。其实,人生处处暗藏因果,只是我们大多不具备洞察玄机的慧眼。无论绕过多曲折的弯路,兜过多大的圈子,都无妨,在你选择放弃以前,真正撞进死胡同的概率微乎其微,要相信,总有路,跑路也是路。只要做好一事无成的准备,继续朝有光的方向前行。
我不敢断言这就是我人生的“底谷”,漫漫人生,前路不敢轻言,说不定哪天还要挨一段更难的路。那段经历,我愿称之为低谷,但绝非底谷。所以,我确实不知该怎样一言以蔽之。只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位人生几经沉浮的长辈讲过的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深山老林的一座湖中住着两条鱼,他们相约有一天要一起去看大海。他们在湖中经过漫长岁月,吸纳天地精华,终于幻化成为两只鹰,一跃冲天,朝着大海的方向齐飞。旅途中,他们被猎人发现,猎人射出了箭,一只鹰为掩护另一只鹰,中箭跌入深渊。得救的鹰痛不欲生,为完成夙愿,更加拼命地飞。终于,大海被鹰找到。他孤独地伫立在山崖,听着浪涛,暗自神伤,日复一日,几乎快要饿死。直到有一天,鹰在入海口看见一条鱼腾空跃出海面,便不假思索地飞上前去将其捕回山崖,这才发现那条鱼正是自己当年的同伴。鹰后悔万分,奄奄一息的鱼却欣慰地说,大海终于也被我找到了。鹰问鱼,可你是怎样来到这儿的呢?鱼说,我的翅膀被射中,跌落谷底后又变回了鱼,幸运的是,那是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我想,我原本就是一条鱼啊,我还可以游啊,你瞧,如今我们又是一样的了。鱼说完,满足地死去。
并非每个人都有羽化成鹰的运气,但我们至少都曾为鱼。
文|郑执